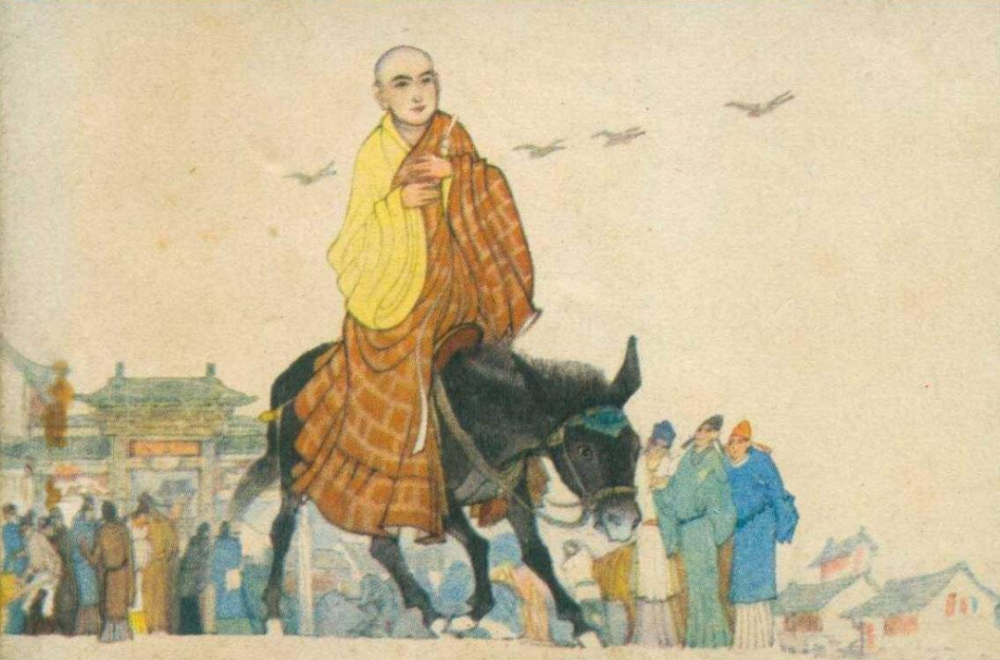弹吉他的戈多伊
文|郑卓文
弹吉他的戈多伊
文|郑卓文
我在酒吧落座,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坐在酒吧一角,和另外两位吉他演奏家在候场。他约莫60多岁,山羊胡子灰白,同样灰白的头发被一根发卡卡在脑后,满身艺术家范儿。
安德烈斯·戈多伊,来自智利的独臂吉他演奏家,到场的几十号人,大多是冲着他来的。
在他上场之前,主持人问:“台下的朋友有多少人在学吉他?”举手的人寥寥无几—在安德烈斯·戈多伊面前,基础的大横按都按不好的人是没脸把手举起来的。
10岁那年,祖父祖母送给戈多伊他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12岁时,他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吉他手,一步步接近自己成为音乐家的梦想。然而,14岁那年,一场意外让安德烈斯·戈多伊失去了整条右臂,下肢、肋骨、脊柱多处骨折。继续弹琴,已然是不可能的事。
安德烈斯·戈多伊没有放下吉他,这个顽强的智利人,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单手演奏吉他的奇迹。他用左手敲击、扫弦、勾弦,让吉他同时产生和声、节奏和旋律。一个人,一把琴,就是一支乐队。这个调皮的老头儿巧妙地运用各种方式完成演奏,赋予了音乐新的元素。他偶尔也会炫技,比如,在弹奏第一支曲子的时候,他让琴弦与身边的话筒架亲密接触,完成了一次滑音。
安德烈斯·戈多伊演奏的曲子多是自己创作的,其中一首与火车有关。安德烈斯·戈多伊说,中国的动车平稳又安静,智利的火车很颠簸,每次火车开动之后,乘客都不得不跟着火车的节奏晃动身体,久而久之,智利人都爱上了跳舞。他弹拨琴弦,拍击琴箱,口中模仿着火车飞驰的声音。李健翻唱过一首日本歌曲《车站》,自己重新填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相聚分别,就像这列车也不能随意停歇,匆匆掠过的不仅仅是窗外的世界。”这首歌与安德烈斯·戈多伊的作品应该心意相通—火车在大地上穿行,如同人行走在世间,未必都是坦途,但每段经历都值得珍藏,令人咏叹。
安德烈斯·戈多伊原本应该更早一些来到这座城市,完成演出,但在去年,他又遭遇了一次打击,因为长期弹琴,他的左臂肌肉出了问题,不得不接受手术。重回舞台的他,看上去是那么快乐。
他弹奏写给儿子的摇篮曲,深情又温柔;他用音乐传递人生信念:Something come,something go(一些事到来,一些事过去);他眼神含笑,和着节奏摆动身体。
他邀请观众和他一起完成最后的表演,合唱几句简单的歌词。听了观众的合唱,老头儿直摇头,模仿观众的漫不经心和平铺直叙,然后说:“No,no,音乐不是这样的。”他重新唱了一遍,郑重地把手放在胸口:“音乐,音乐是从这里流淌出来的。”
这是一场由吉他工作室主办的演奏会,主题是“永不放弃”。坦白说,来之前我有点儿担心看到一场苦情戏。但在那一瞬间,我湿了眼眶,不是因为身残志坚、怀揣梦想之类,而是被这位音乐家的诚挚和深情感染。
安德烈斯·戈多伊已经被载入智利的音乐史,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能仅用左手把吉他弹得这么好。他独创的演奏方式,除了是一项不凡的音乐成就,还被认为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价值。
从2007年开始,安德烈斯·戈多伊去往世界各地表演,他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但认识他的人仍是少数。
独臂的安德烈斯·戈多伊为观众展示了吉他的魅力,让人惊叹一件乐器还可以这样演奏。从这一点来说,他和罗纳尔迪尼奥、乔丹等人做了同样的事:展现一件事物的无限可能。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