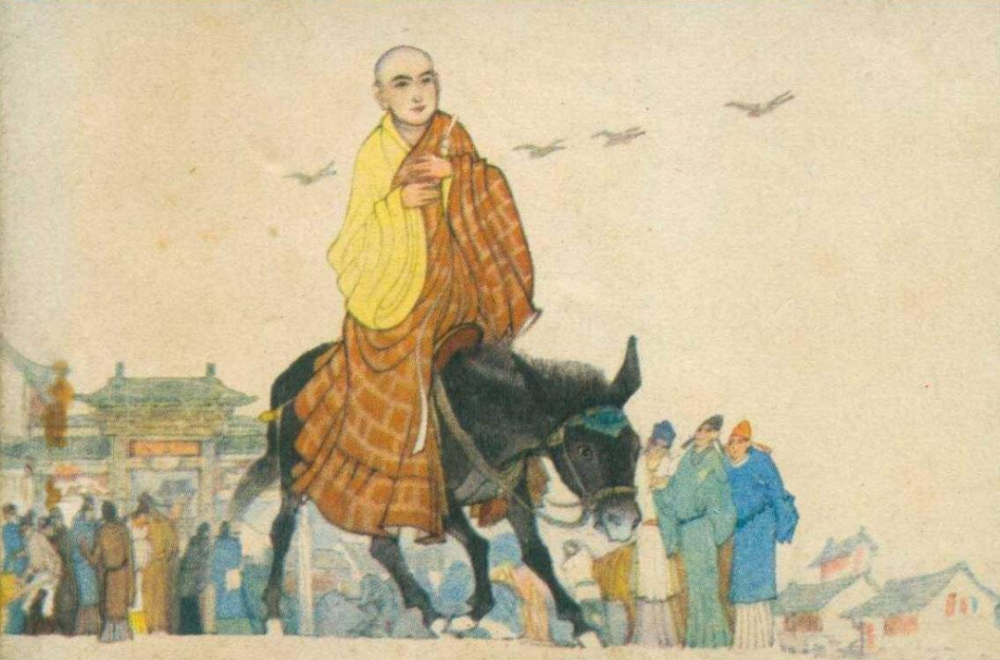为了告别的聚会
文 _ 荞麦
为了告别的聚会
文 _ 荞麦
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流行,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廉价,廉价得让人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在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有50多人,都是1981年左右出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普及了,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在之后的很多年,除了个别同学,其他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不知道。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
我想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的同学组织“毕业十年聚会”,我一反常态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通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句“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地方,而差不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大学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房地产广告业。大学不如房地产能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男生并没有变胖,有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好像这十年,时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小孩,除了我。小孩子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聚。”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然后,大家拼命合影。
如果回头去看,这十年里,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了,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翻到十年前一位劝我去上海发展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志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社工作,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
很不幸,他说的话几乎都对,只有一句话不对: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2003年,还是“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鼓舞我们的时代。十年过去之后,当年这么鼓舞我们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豪迈地讲话了。
最终我们都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人,伴随这一切的是传统媒体的衰落。新闻不再是令人向往的专业了。职业的理想早就丧失了,命运却还没有展示太多威力。再等十年,我们可能才会看清楚命运的轮廓。现在我们言笑晏晏,意识到自己是被很多无奈和平庸所包围的一代,却透露出一种集体性的淡漠。
有个同学说:“这么单纯的聚会,单纯到令我受不了。”确实太单纯了,没有利益关系,谈不上多么深刻的友情,同学间没有谈过恋爱,连八卦都欠缺。我们仅仅是因为种种巧合,一起在当时还鸟不拉屎的新校区待了三年,后来又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宿舍里经常有耗子。有些人读了我那本写青春回忆的《最大的一场大火》,里面几乎找不到同学们的影子,但还是有人声称看得掉下泪来。只有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因为我写字,他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还在挣扎什么。
十年之后,又遇到禽流感,但大家没有那么恐慌了。每个人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脸上也都能恰当地露出笑意。相聚的意义是我们可以为对方的青春证明。背景音乐当然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横幅上贴着一些老照片、一些新照片,放在一起才知道我们确实经历了时间。也要对着照片互相提示,我们才能完整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们拥抱、微笑,不谈论这十年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幸福、快乐或者失落、痛苦,不倾吐心事。我们举了举杯,但没有人醉,没有人哭,也没有人感慨。所有想象中“毕业十年聚会”会出现的场景,都没有出现。
这天下午,我在书店有个活动要参加,一个现在依然很瘦的男同学自告奋勇用他的电动车送我去书店。在滚滚车流中,我把手放在他的腰上,摸到他腰部一圈薄而结实的赘肉。就在那一刻,我一阵轻松,放下心来。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在每个人自己才知道的地方。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