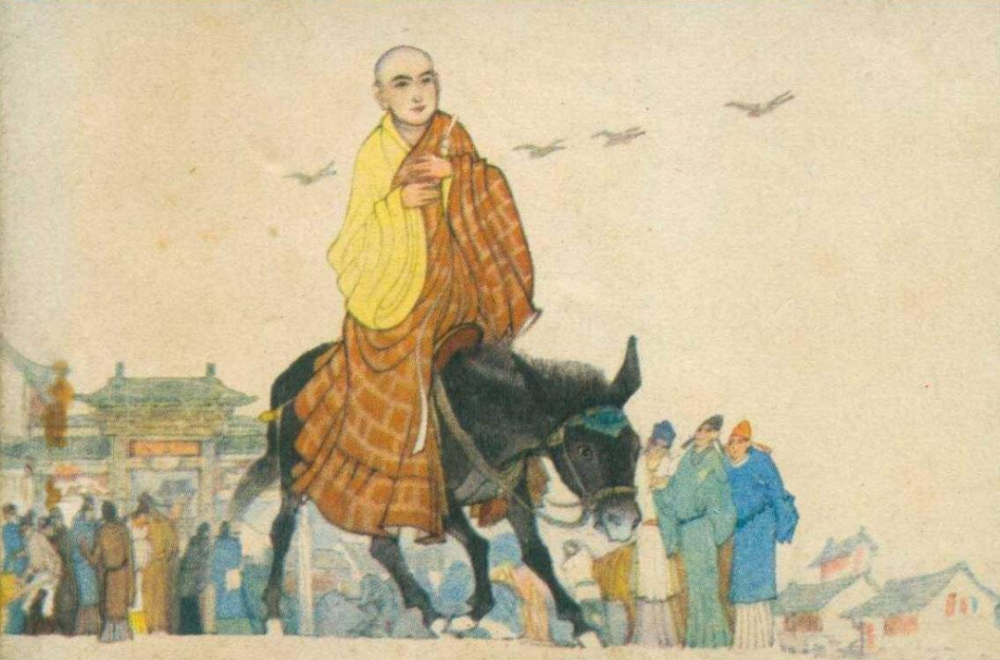二 娃
文 _ 苏晟
二娃是我的高中同学,一段时间的同桌。2008年5月12日,正在四川银厂沟游玩的二娃,不幸遇上了那场众所周知的大地震……事后我百度过图片,那里有水的地方几乎都被填平了。
“要是他还活着,现在肯定是个非主流。”“不,他生前就够非主流了。”前些日子,我跟高中同学聊到二娃。我们班没几个人比我更了解他,因为没有谁像我这样,真的在乎过他。
2000年8月,我认识了二娃。当时高中新生军训,大伙都穿一样的服装,理同一个发型,人与人之间没啥区分,但二娃就是那么打眼。全排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走正步不仅肩膀耸得老高,还一贯同手同脚。我正好站他的后面,心想这不是个白痴,就是个天才,反正不是正常人。二娃那个正步,幅度倒是大得很,但一直在原地弹上弹下,这让站在他后面的我,经常会不小心踢到他。每次被我踢到,二娃都会第一时间转头对我来个“邪恶凝视”。好怕怕啊,被他这样一番凝视后,我通常都会下意识地放缓步伐,然后被我后面的人踢中屁股。
军训间隙,二娃的话很多,什么“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是个大阴谋”“打《星际争霸》我可以单挑你们所有人”“我打篮球从来不穿公牛队队服,因为怕别人误以为我是乔丹”……这些无厘头的言论我至今都记得,就像他当时迷彩服背后白色的盐渍一样清晰。
总共十天的军训,我们和二娃只相处了六天。因为第六天晚上,二娃的妈妈得知宝贝儿子挖鼻孔挖出鼻血后,就赶紧泪流满面地打车过来将同样泪流满面的二娃接了回去。后面的四天,挖鼻孔导致伤退的二娃,基本会出现在我们每次的闲聊中,每次出现,都会让我们忍不住大笑特笑。
正式开学后,“伤愈复出”的二娃成了我们开玩笑的首选。
“二娃,流鼻血就好好待家里养着嘛!”
“滚,我就是流一星期也不会有事的。”
“一星期?二娃原来是妹子哟。”
开学后不久,就遇上年级里打篮球联赛。我们班打篮球的没几个,二娃毛遂自荐做了队长,张罗组队,结果第一场就惨败。第二场,二娃破例穿上他尘封多时的公牛队23号短裤,结果还是惨败。最后一场输得倒是不多,但队长二娃在赛前就被他的队友一致改选为拉拉队队长。从此以后,那个立志要带领我班“全国制霸”的“乔丹”就正式“被退役”了。
二娃性格不错,从他能接纳“二娃”这个外号就能看出,除此之外,貌似就再没优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学期后,班主任会把我换成他的同桌。我为此郁闷了有一阵子,因为在我眼里,二娃就是“不可理喻”的代名词,一个校运会跑1500米被倒数第二名甩了有一整圈,赛后还好意思去找裁判告状,说跑他前面的全部犯规了的怪人。如果要在那时候给他贴上标签,我会贴:神经病、厚脸皮。
当年,我是花钱才调招进这所重点高中的,内心的自卑让我进校后一直很低调。二娃也是调招进来的,但他一点都不低调,总说自己是因为中考考数学时最后一页看漏了,全是空白,才与我为伍的。跟他坐了一段时间后,我大致相信他空白了一整页,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做。
对于老天安排这样一个同桌给我,我只能归因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二娃话超多,有回自习课,他说:“那个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你看没?我觉得岳不群演得还不错。”我刚答了声“哦”,就被班主任逮个正着,两人被罚打扫一周卫生。我气得要死,从此他跟我说话,我也是爱理不理,一直到那一天。
那是高一下学期期末,物理老师要带我们去户外做反冲实验。虽然给了一周的准备时间,但大家无非就是周末去地摊买根“冲天炮”什么的。唯一的例外是二娃,这家伙在实验当天整了一口袋的东西来,然后就在大家都午睡时,自个儿在座位上鼓捣。过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睡前,摆在他桌上的是几摊粉末,我醒来的时候,粉末就变成了火焰……那一刻,整间教室都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和女生的尖叫;那一刻,他惊慌失措地盯着火焰,我盯着惊慌失措的他;也就在那一刻,不知是看到了他眼睛里火焰的投影,还是他眼睛里闪烁的光,我突然觉得我旁边这个神经病、厚脸皮—“哎哟不错哦!”
事后,因为“损害公物”,二娃被罚款200元外加再次打扫卫生一个礼拜;事后,二娃有了我这个朋友。进一步接触中,我发现二娃这家伙知道的东西还蛮多的。比如,爱斯基摩人用冰箱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食物结冰;眼镜蛇要是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也是会死的,等等。但统统比不上任达华和徐锦江是三级片专业户来得震撼,二娃跟我说这些时,我听得像个白痴一样张大嘴巴。
高中第一个暑假,我和二娃来往颇为密切。每次接近中午打电话到他家,他妈妈都会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要我不要影响到她宝贝儿子的宝贵睡眠。我去过他家,还进过他卧室,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一张很大的美少女战士的海报。之前他曾瞧不起我视星矢为一生偶像,于是我也就代表月亮鄙视他,“哟,几岁了?还美少女战士。”靠窗的地方有个大书柜,里面除了《走向清华北大》《三点一测》《黄冈密卷》之类的辅导书外,还有很多课外书和漫画书。在后两种书的映衬下,那些辅导书都显得异常的新,显然很少得到二娃的临幸。我很羡慕二娃有张漂亮的书桌,相比之下,我的“书桌”从来都是饭桌和缝纫机客串的。我更羡慕二娃书桌上放的那尊大概半米高、没穿衣服的日本动漫女主角,羡慕得忍不住想伸手摸一把,这时二娃就会喝住我:“住手!这是我的女神。”
说来惭愧,我也算全班第一批知道二娃噩耗的,但也是在“5·12”地震一年多以后了。高二再次换座位之后,仅仅有两天的不习惯,我就跟美女同桌相见恨晚了。此后,二娃迷上了《传奇》,一放学就往网吧里钻。有阵子他卖游戏装备赚了近2000块钱,一时间,年级上的混混,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乖乖地跟在他后面,到处吃喝,洗脚按摩,直到花光他所有的钱。
我跟二娃最后一次单独见面,是在高三的第一个周末,同是9月出生的我俩,相约在18岁前,一起过个成人礼,地点在成都游乐园。我记得我们那天吃了德克士,玩了翻滚列车,坐了摩天轮。当然,在摩天轮上,我们并没有拥吻……
上了高三,我跟我的美女同桌好上了,恰巧,她又是二娃众多心仪妹子中的一个。我问二娃:“你没事吧?”他说没事。一周之后,我被同桌甩了,二娃问我:“你没事吧?”我说鬼才没事。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恋,直接导致我在学习上小宇宙爆发,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变态冲刺。在此期间,我斩断了跟很多人的交集。
第二年9月,我成为大学新生,二娃在一所不知名的高中开始了他的复读生涯,从此消失。此后几年,不时有他的传言,在哪年加入了成都某支CS战队,参加了全国大赛;又在哪年只身骑单车从成都进西藏……总之,都不知真假。跟二娃在同一所大学念书的高中同学说,在校期间二娃只找过他两次,一次找他借了100块钱,另一次见他不在就找他室友借了100块钱,反正都没还。
3个月前,我辞职骑了趟川藏线,在翻越折多山之前,在折多塘一家小旅店的墙上无意中看到有“2006年7月11日,二娃在此一宿”的字样,结尾处还有个闪电符号。我一下子怔住了,难道是他?那个迷恋过哈利·波特,脖子、手背全是闪电标记的疯子?静了几秒,我掏出笔,紧挨着这行字的下面,写下“2011年7月11日,二娃的同学在此一宿”……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